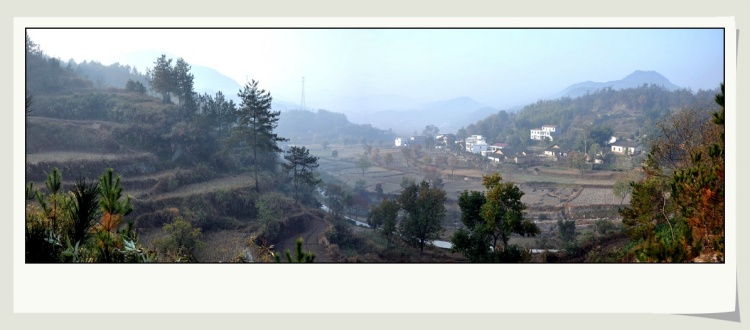中医学术流派及学术思想、学说形成及其它之我见--鲁兆麟+中医药理论的哲学基础--鲁兆麟
luyued 发布于 2011-04-30 16:17 浏览 N 次国家中医药发展论坛(珠江论坛)发言稿
中医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具有中国文化深厚的传承底蕴,历史上经历了数千年的传承与发展,出现了数以千计的中医名家,具不完全统计,在中医名人辞典中,曾有六千人左右,有著作一万佘部,在这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名医辈出,中医研究不断创造出一些新的学术见解、学术观点,然而建立在中国文化底蕴上的中医药学不像建立在物理化学数学基础上的西医药学一样,掌握某种治疗疾病的方法或技术,提高治疗水平,便于推广与普及,故尔,相比之下,表现的发展速度缓慢,而且每一种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很难让大家认同,究其原因,是中医药学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人与自然统一,人的建康受到社会的影响,站在人即是自然人又是社会人的理念基础上,因此中医提出了诊治疾病维护健康的基本规则,强调人与天地相应,强调七情可以致病,强调治病应以八纲为辨证的纲领,提出了辨证论治的指导性原原则,提出了因人因地因时制宜的治疗法则,提出了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治病理念,提出了“仅察阴阳以调之,以平为期”的治疗大法则,提出了“恍惚之数,生于毫厘,毫厘之数,起于度量。“ 是对人体健康思想被很多中医学家所接受、所影响,到了金元时代,人们站在这一全新的角度审视中医药学,提出了中医药学也应该站在这一角度去研究与发展,故尔,在这短短的历史时期,出现了一直影响至今天中医药发展的著名金元四大家:刘河间(刘守真、刘完素)、张从正(张子和)、李东垣 (李杲、李明之)、朱丹溪(朱彦修、朱震享)。而且各立门户,被后世尊为四大医学流派的创始人,刘河间被尊为寒凉派的创始者,张从正被称为攻下派的鼻祖,李东垣被称为补土派的开山,朱丹溪被称为滋阴派的创建者。其它医学流派虽然也被后学所接受,但应该看到,为什么短短的金元历史时期会出现这么多影响中医药发展的重要历史人物。另外,大家都公认张仲景为医圣,其著作《伤寒论》奉为四部经典之一,这一说法的提出,应该也是在金元时期。刘完素《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曾评价张仲景为“医门之孔子,亚圣也。”既然张仲景为圣人,他的著作就被称为经,因此《伤寒论》自刘河间以后,就变成了只能全文注解,不能随意改动,因此,宋以前的《伤寒论》书籍没有完全按原文撰写者,而金元以降,没有一部改动原文的书,即使改动原文,也要阐明理由,故尔明清时期出现了錯简重订派。可以这样说,中医发展经过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从《黄帝内经》直至宋代,基本是医药分开研究,中医理论研究侧重于理论探讨和疾病现象的研究,方药的研究侧重方药的积累,侧重经验方的收集,因此,到宋代经验方的积累已经有相当数量,孙思邈《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就收集处方五千多首,王涛《外台秘要》收集古代医书近七十多种,方剂6756首,两位医家就收集了一万多首,据统计全部中医古书中方剂有方剂名称的近十万首,无名称的方子有近三十万首,加在一起近四十万首,这么厐大的方剂库任何人也难以把握,出现了中医药防治疾病的困惑,宋代理学思想的影响,格物致知理念的提出,强调穷理思想,中医一些学者受其启发,开始反思中医学发展之路,然后深研中医古代医书,发现张仲景的《伤寒论》有很高的临床实用价值,而其提出的“脈证并治”思维具有与“穷理”思维的一致性,因此张仲景的学术思想被剂河间大力宣扬而被后世医家所接受,辨证论治形成中医诊病治病的特色,辨证的疾病认识观就将中医理论、中医诊法与中医病机紧密结合在一起,而论治又与中药、方剂、針灸、按摩结合在一起,使中医中药结合成一致的一整套从理论到临床、从诊断到治疗的完整学科。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发展与中医药学的发展是互相影响和互相推动的。在这一大思维指导下,众多医家不断从各个角度各各方面探索中医药学的发展,明代出现了以脏腑为中心的各种学说,各种学术思想,出现了温补学派。到了明末气候变化,出现了很多以发热为主体的传染性疾病,而且运用《伤寒论》方法治疗效果不能满意,人们运用穷理方法探索其病机,并结合前人的经验,提出了温病学说,创立了温病学派。明代时期,国际上交往日趋增多,文化交流益日趋频繁,西方医药学知识也传入中国,隨着西方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的发展,对人体生理病理现象认知的深入,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中医西医汇通结合的思考,故尔明清以后,又出现了汇通学派,虽然汇而未通,但是这种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还是值得鼓励的。当然,学派的划分有不同的方法,这一点自古以来就存在,比如一直流传的南方派与北方派,就是以地域划分的学派,又比如现在各地区自称的学派如岭南医学、錢溏医学、吴中医学、孟河医学、新安医学、燕京医学等等,各有其学术特征和治病特点,可以又称作学派。这一研究方法符合中医理论因地制宜的思维,无可厚非。今后地域医学还是直得大力提倡的。因为中医非常关注保一方平安的仁慈之心、大医精诚的理念的。
学说的形成具有中医的特点,每一种学说或者学术思想都是从宏观角度探索人体健康与疾病出现的病因病机诊法治疗等等方方面面的见解与看法,能够形成一整套说法者就是一种学说,如果仅仅是在某一方面有自己的看法,又不夠成系统,应该说只是一种学术思想。学术观点,或者是一种临证经验只是在更小范围的見解看法而已。对于学说、学术思想不要动则提及,而应当审慎使用。
中医药学包括中医和中药两大部分,作为一个医生,掌握看病和运用中药、处方,而对中药处方的掌握也应当站在中国文化底蕴的基础上去掌握和理解,我曾对中药学、方剂学进行学习研究,发现古代中药学的专业著作的编写,都是以动植物分类,而《药性赋》歌诀是按寒热温凉药性分类,金元张元素在其《医学启源?药类法象》提出了药物分类,分为五类:风升生、热浮长、湿化成中央、燥降收、寒沉藏。並没有以药物功效主治分类的,而唯独现代编写的中药教材确是以中药功效主治分类的。中药的理论是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引经。这些理论不能很好的解释中药的功效主治,而这些只能解释药物作用于人体的作用趋向和对人体的整体治疗作用,也可以称作“药象”,也就是说中药于人体的作用包括两部分:整体作用趋向和具体功效作用,而中医运用中药治病时是在关注人体整体状态的同时又关注具体病症,才能处以很好的中药复方,取得满意的疗效。因此,掌握深厚的中医药学文化底蕴,对于传承、发展中医药学。对于掌握中药学的基本知识和临床应用都大有禆益。除此之外,对于方剂的理解也应当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去认知,不能考虑过于简单。以方剂学教材为例,目前方剂学教材中的理论仅仅局限于君臣佐使一种,其中只有半夏泻心汤一方运用了气味理论加以阐发的,这对方剂学的理解有所偏颇,缺少了中国文化愽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对于深入掌握方剂精髓、方剂配伍思维是有不夠全面的影响,因为对于方剂配伍在中医中一直有多种方法,除了君臣佐使外,不有气味配伍、升降配伍等,气味配伍源于《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说“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湧泄为阴,淡味渗洪为阳。”提出了五味作用趋向,金元时代成无己是第一位研究方剂治病原理的,他在解释《伤寒论》方治病原理时运用的解释方法就是用气味配伍解释的。而后金元医家张元素《医学启源》曾提出方剂气味配伍方法,其解释当归拈痛汤方解云:“治湿热为病,肢节烦痛,肩背沉重,胸膈不利,遍身疼,下注于胫,肿痛不可忍。经云:湿淫于内,治以苦温,羌活苦辛,透关利节而胜湿;防风甘辛,温散经络中留湿,故以为君。水性润下,升麻、葛根苦辛平,味之薄者,阴中之阳,引而上行,以苦发之也。白术苦甘温和中除湿;苍术体轻浮,气力雄壮,能去皮肤腠理之湿,故以为臣;血壅而不流则痛,当归身辛,温以散之,使气血各有所归。人参、甘草甘温,补脾养正气,使苦药不能伤胃,仲景云:湿热相合,肢节烦痛,苦参、黄芩、知母、茵陈者,乃苦以泄之也。凡酒制药,以为因用。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猪苓甘温平,泽泻咸平,淡以渗之,又能导其留飲,故以为佐。气味相合,上下分消,其湿气得以宣通矣。”基本是将君臣佐使理论与气味理论相结合阐发方理。尔后,清代著名温病学家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论方剂的作用时,将桑菊飲、银翹散、白虎汤、等,均以气味来论方,故以辛凉轻剂桑菊飲、辛凉平剂銀翹散方、辛凉重剂白虎汤方命名,说明吴氏论方剂十分重视方剂中药物气味配伍;又如在解释清宫汤方时曰:“此咸寒甘苦法清膻中之方也。”至于升降配伍,另有杨栗山《伤寒温疫条辨》创立的升降散,该方由姜蚕、蝉蜕、姜黄、大黄四味药组成,为治温病的总方,“以姜蚕为君,蝉蜕为臣,姜黄为佐,大黄为使,米酒为引,蜂蜜为导,六法俱备。”其方又名赔账散,又名太极丸,杨氏以方用“姜蚕、蝉蜕升阳中之清阳,姜黄大黄降阴中之浊阴,一升一降,内外通和,而杂气之流毒顿消。”其创立的治温病十五方均是以升降散为基础变化而成。这种思维来自《黄帝内经》,《素问?六微圣旨大论》云:“出入废则神机化滅,升降息则气立狐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提出了宇宙万物都应当符合这一规律,中医方剂学也应当如此。以上可見,中医方剂理论中蕴藏着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必须把它阐发清楚明白,让学者深刻领悟,才能对中医药有深入掌握的可能,再者医生要给病人诊病维护健康,而中药是一个有力的武器,掌握中药方剂是不可缺少的知识,对中医理解与提高是十分重要的。因此,中国文化底蕴包括中医的各个方面,不仅仅只是中医理论、《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等历代名家的学术思想及各个学术流派的中医认知,而是包括中医的方方面面,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以上是我个人学习中医、研究各家学说的一些想法,其中也包括我对中医的感悟,不一定正确,欢迎各位同道及专家指正。谢谢。
中医药理论的哲学基础--鲁兆麟
本文引用自白术《中医药理论的哲学基础--鲁兆麟》
中医药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其发展过程中,一值受到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具有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中医药的理论体系的形成始于《黄帝内经》,《内经》成书于战国时代。春秋战国时期正是我國重大的历史性变革时期,社会的变革,奴隶社会的解体,封建社会的形成,促进社会的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推动了文化的進步,中国文化得到了空前的進步,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诸子百家的文化盛况,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对这一历史时期的描述和评价。诸如孔子、孟子、老子、韩非子、庄子、管子、孙子都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先后出现的。他们的思想对社会的发展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医药学同样受到其深远影响。中医学在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由经验的积累到理论认知的过程。在《黄帝内经》成书的时代,又同时出现大量的经验方。《汉书?艺文志》曾记载有医经七家和经方十一家,医经七家包括《黄帝内经》、《黄帝外经》、《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白氏内经》、《白氏外经》、《白氏旁篇》。经方十一家包括载有《五脏六腑痹十二病方》、《五脏六腑疝十六病方》、《风寒热十六病方》、《金创方》等。这说明早在《黄帝内经》成书的同时,中医学已经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与此同时,在《灵柩?经水》一篇中又记载了对人体解剖、生理现象的大量文献资料,并指出:“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皆有大数。”等等,说明中医学在《黄帝内经》成书时代对人体的生命现象的认知己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同时对疾病治疗亦积累了相当的经验。但是仅凭这些简单的知识和认识水平,要想用以解释和说明中医学临床千变万化的疾病是十分困难的。中国古代的先人们十分聪明,他们借助当时丰富发展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将人体的解剖知识与中国哲学思想巧妙的结合在一起,运用丰富的哲学思维来解释人体的各种生理、病理现象,解释各种疾病的治疗原则和中药的治病原理,解释自然界对人体生命活动的各种影响。中医学借助于中国古代哲学来认知自然科学的人体生命现象,不可能将生命现象认识的十分具体,而只能是宏观的认识其一般规律,把握其总体的规律与现象。借助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些认识来构架中医的理论,必然形成其宏观认知的思维,而对具体的的认识往往不能够很好的了解,因此,在《内经》的书中包括了先秦诸家的思想,故此,《内经》这部著作不仅是中医学理论的渊薮,而且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中,亦占有一席之地。中医学既然受到中国古代哲学的深刻影响,是以中国古代哲学为其理论形成的指导思想,而哲学是指导自然与社会各个领域的科学。但哲学对科学的指导应当是宏观的,不可能认识到微观,因此中医学从它建立起理论框架开始,就建立了一种宏观思维方法,它使中医药学的发展并没有沿着微观分析的思路向前发展,而是一方面仍然注重着治疗方法的积累,另一方面,又在探索中医治疗疾病的原始思维。至汉代,著名医家张仲景撰写《伤寒杂病论》,强调注重对人体整体状态的把握,提出关注临床脉证的辨别分析,强调了方证对应的关系,提出了六经辨证的新思维,因而张仲景被后人尊为医圣,《伤寒论》也被后人尊为经典之一。说明中医对思维方法特别重视,也说明中医的思维方法特别重视人体的整体状态。这一点早在中医理论奠定的代表著作《黄帝内经》中就已经充分体现出来。《素问?灵兰秘典论》曾说:“恍惚之数,生于毫厘,毫厘之数,起于度量。”明确提出了中医的思维方法。意思是说:通过具体的诊查了解人体的可以把握的各种表现,包括身体的胖瘦、气色的明亮晦暗、声音的洪亮与否、呼吸的是否正常、肢体的活动、舌苔与舌色、脉象的表现等可以度量到的表现,运用中医理论加以分析,得出恍惚的结论,即对人体整体状态的评价,又是中医对健康与疾病的评价方法。这是一种形而上的思维模式。古人有“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可以说:中医的思维和现代西医的思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思维模式。中医更强调对人体的整体评价,而西医是在解剖学和物理、化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更强调人体的疾病的具体病理变化,所以中医十分重视对人体的调整,西医十分重视具体疾病的病理治疗。这是中医构架理论体系与西医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截然不同之处。即中医强调对人体整体状态的分析研究,而西医则更重视具体疾病的研究,这是中、西医之间的差异。当然,中医在关注人体整体状态的基础上,也重视具体的疾病,而西医在关注具体疾病的病理变化的基础上,也重视人体的整体情况,但是,两者的侧重点不同,故而,形成了不同的治疗思维,形成了不同的理论体系。
因此,中医学的理论框架基本上是以宏观的理念为最高的理念,如阴阳、五行、精、气、神等成为了中医学的最基本理论,進而,又结合对人体的简单形体的实体认识和生理病症的观察,衍生出很丰富的理论内容,但这些理论主要是为了解释各种现象的宏观认知。当然,中医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并没有放松对具体问题的解决办法,因此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一直不排除各种治验方的积累,到了唐宋时期,发展到了鼎鼎盛阶段,以治病方剂为主要内容的书籍大量出现,除了与《内经》同时出现的经方十一家而现在已经遗佚的十一部方书二百七十四卷外,又出现了王焘著的《外台秘要》、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及宋代的《太平圣惠方》等。至明代《普济方》到了收集方剂6万余首的规模。然而,方剂的积累并不能囊括所有的治疗方法,又令医生无法掌握,再者,其与中医药理论不能很好衔接,导致理论脱离临床。因此,中医药学并没有沿着这一条路向前发展,而是一些医家又迭用了另外一条思路,即《内经》所创立的形而上的理论为指导的对人体生理病理认知的思维方式。汉代著名医家张仲景撰写了《伤寒杂病论》一书,首次将辨证思维运用于中医学中,强调中医认识疾病必须把握证候,将“证”的概念引用于其中,这样,中医学就将《内经》的理论与临床紧密结合在一起。正如张仲景在其序言中所说:该书是“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胎胪药录》,合成《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强调其与《内经》的理论认知是一致的,即均是形而上的思维。以后,直至金元时期,理学盛行,影响到中医药学的学术发展。“格物致知”的理学观念影响并形成了中医学的辨证论治的临床思维模式。可以说,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核心思想是对人体状态的整体把握,形成辨证论治的临床认识病证的思维方式是其发展的必然结果。
首先,中医学将气的概念引入其中,认为气是构成一切事物的最基本的基础,一切事物都是由气所构成的。中医学将人体的各种形体存在及各种生理、病理表现均从气的理论角度加以解释说明,《黄帝内经》中明确提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天地合气,命之曰人。”气是构成世界万物包括有生命的动植物和无生命的各种物质,也是有生命的人体的最基础的物质和生命活动能力的来源,既人体之精与人体之神的来源。共同构成了人身三宝精气神。“气”是中国哲学中的重要范畴,古代哲学家认为气是构成自然界一切事物的本源,这些哲学家的这一观点被后世总结为“气的一元论”观。在此基础上,中国历史又出现了以宋妍、尹文为代表的宋尹学派哲学家管子,管子提出了精气说,认为宇宙自然界的万物都是由精气所构成的,《管子》诸篇为其代表,这些学者对精与气的关系论述提出:“精者也,气之精者也”。即精与气二者虽然名称不同,各有各的范围,但二者又是密切相关的。即二者之间虽然名称不一,精是构成宇宙自然界有形之质的基础,就人体而言,人体中的有形之质包括固体的各组织器官,如肌肉、脏腑、五官九窍:也包括人体中存在的精、血、津液等等有形液体统属于“精”的范畴。气是构成人体中无形之质,它是一切有形之质的化生基础。精气的关系是有形与无形的关系,即有形之精源于无形之气,无形之气化生有形之精。故在《内经》中既有“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的论述,又有“人始生,先成精”的论述,更有“阴阳离决,精气乃绝”的说法。这说明在中医学的核心理论中,既有“气的一元论”说,又有古代哲学家的“精气说”,是两种哲学思想的巧妙的结合与统一。气是人体物质基础和生命活动能力的本源,精与气既然有密切的相关性。说明中医学中的精也包括人体的各个有形组织噐官及其生命活动,也具有形神一体的认知观。以此言之,中医学是建立在物质与功能统一的认识观基础上形成的,既形神统一的认识论,故《黄帝内经》中强调人的养生长寿要求“故能形与神倶,而尽终其天年。”要求人体健康须要“阴平阳秘”才能作到“精神乃治”。正因如此,故中医学在《内经》形成的时代即建立了七情致病的学说。《素问?调经论》有云:“怒則气上,喜則气缓,悲則气消,恐則气下,思則气结,惊則气乱。”强调神的失常往往是人体气机失调的重要原因,即人体形体失调的产生与精神的失常密切相关。《内经》中这类的论述非常多,如怒伤肝、喜伤心、思虑伤脾、悲伤肺、恐伤肾。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形成了七情与五脏相关的理论体系,用以指导临床。
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医理论影响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其中庸思想,中庸思想来源于孔子的儒家思想,强调世界万物的存在要其既无太过又无不及,人体的生命亦是如此,人体的健康就是身体的各个方面处于中庸、平和状态,既《内经》所说的“阴平阳秘,精神乃治”。和、合、平三者,在《内经》中多处加以论述,又如《内经?至真要大论》“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如果人体阴阳两个方面中任何一个方面出现了偏盛偏衰,就会出现人体不适的状态,故《内经》提出“阳胜則阴病,阴胜則阳病”。“阴虚生内热,阳虚生外寒”。对于脏腑功能的描述,中医学在建立其理论时亦十分强调其对立双方的统一协调,在论述五脏功能时,提出肺主一身之气,同时提出肺又主宣发和肅降,二者的协调与统一,才能维持其主一身之气的功能;肝主疏泄又主藏血,只有肝的这两个功能维护正常,保持协调统一,才能维持肝的正常功能;脾主运化水湿与运化水谷精微,但脾气又主统摄血液,二者一个功能主疏通于外,一个功能主收涩于内,一开一阖以维护脾的功用;心主藏神于内,又主血脉运行于外,二者协调统一以维持心脏功能正常;肾主藏精,又主全身气化,一藏一行,共同完成肾的各种功能活动。以此观之,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是依靠各自的和谐,即儒家所说的中庸之道。不仅如此,在脏腑功能之间亦存在着相互配合协调的中庸之道,如肝与肺的关系,有“肝升于左,肺降于右”之说,心与肾之间存在着心火宜下降,肾水宜上济的认识,即“水火既济”“心肾相交”“坎离既济”,脾与胃二者之间亦关系密切,脾主升而胃主降,脾主运化而胃主受纳,二者相互配合,以共同完成其对水谷精微与水湿的代谢。这些认知无时不在的说明中医理论中处处都受到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是在儒家中庸思想指导下形成的。
中医基础理论中的核心理论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本身都是中国哲学范畴,阴阳学说起源于周易,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对于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除了其相互的对立、消长、互根和相互转化外,更为重要的是阴阳的一体观。阴阳的一体观在《内经》中早有论述,如《阴阳应象大论》云“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其要一即是说“一”是阴阳理论的核心观念,只有两个相互对立的事物或个体,能够统一于一个事物之中,就具备阴阳二者之间的各种关系,如果不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不能相关,中医学中这种相互关联时时存在,例如营与卫是气的两个方面,一行于脉中为营,一行于脉外为卫。故在脉外之卫属阳,而脉中之营属阴,若以营与血相互关系来分阴阳,则营是血中无形之气,故属阳;血是脉中之有形之质,故属于阴。同一个“营”,在不同的阴阳范畴之中,其属性绝然不同,这说明它们在不同的“一”的前提下,会出现不同的属性。由此言之,“一”是“二”的前提条件,只有明确“一”是指什么样的具体事物,才能分析“二”的阴阳属性,故张景岳曾说:“阴阳者一分为二”。可见阴阳学说的一体观是阴阳学说的理论前提,是阴阳学说的最重要内容。至于阴阳学说的其它具体内容,包括阴阳的互根、阴阳的消长、阴阳的对立、阴阳的转化等内容,都是在阴阳一体观的前提下才具备的。
至于五行学说,其本身亦是一种哲学范畴,最早的思想是强调宇宙自然界是由五种基本物质所构成的,由它们化生万物,即万物都是由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所化生的,而五种物质各有其特性,木曰曲直,火曰炎上,土曰榢啬,金曰从革,水曰润下。而后以同类归属的方法将宇宙万物归属其中。而且强调五行之中的任何一行与其他四行之间均存在着相关性,称之为相生、相克、相乘、相侮。任何一行都与其他四行之间存在着生我、我生、克我、我克、侮我、反侮的关系,强调了多种事物之间的复杂关系,五行学说与阴阳学说互维补充,相互结合,构架成了中医学基础理论的思维模式,用以说明人与自然界出现的各种简单到复杂的现象,这一将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统一起来应用于说明人体的生理与病理现象,将中医理论纳入古代哲学思维方法中去思考与认知。同时,《内经》一书也是中国古代典藉中最早将二种哲学范畴结合起来進行实际应用的一部著作。
正由于中医是建立在整体观、气一元论、精气说、形神一体关、人与自然统一观的基础上,因此,中医就形成了自己的辨证论证体系,汉代医家张仲景写了《伤寒杂病论》,在书中明确提出脉证并治,其书被称之为辨证论治的典范,奉为经典。但在唐宋时期,人们为了关注健康治疗疾病,曾经用很大精力收集整理治疗疾病的方药,整理了很多有名的方书、如《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但将理论与方药紧密结合,颇显不够。并未构架完整的辨证论治体系。
中医学在其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其学术发展在金元时期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在这短短的历史时期曾出现有名的金元四大家,探讨中医病机理论,对后世中医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使中医学的辨证论治的思维方法得以发扬。中医学的这一深刻变化,归结于与中国文化的深入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归结于中国古代哲学家哲学思想的進步,到了宋朝,中国文化有了明显的变化,除了道家之外,佛家亦传入了中国,除此之外,儒家也有了很大发展,形成了儒、释、道三家三足鼎立的局面。这时,以程颐、朱熹等一批哲学家,提出了理学的观点,强调“理在气先”、“格物致知”的认识,融儒、释、道三家为一体,创立了理学。这一学说被宋代统治者大加弘扬,被广泛推崇,因此,理学思想影响了中医学的发展,一批中医学家接受了“格物致知”的理念,开始探讨中医疾病产生的原理,探讨中医的病机,刘河间注重《内经?至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条的研究写成《素问病机原病式》专门探讨病机理论,创立了“六气化火”学说,被后世成为“寒凉派”;张元素深研《内经》理论,写了《医学启原》,探讨五脏病机,创立了五脏辨证的雏形对后世脏腑辨证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李东垣师承张元素,对脾胃病机深入研究,撰写了《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兰室秘藏》等书,提出了“脾胃内伤,百病由生”的观点,对脾胃病的辨证独有发挥;朱丹溪早年随朱熹的弟子许谦学习理学,后弃儒从医,拜罗知悌为师,潜心研究,终成大家,撰写了《格致余论》等,以理学的观点阐发医学理论,创立了“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观点,提出了杂病治疗注重气、血、痰、郁四方面,成为著名医学家,张子和私淑刘河间学术思想,提出“病由邪生,攻邪已病”,善用汗、吐、下三法治疗疾病成为有名的“攻邪派”的代表医家。由于,金元时期众多医家对病机的发挥,使中医学的发展有了根本的转变,由治病的思维转向治疗病机的思维,由方药治病转向方药治疗病机,即从治病向辨证论治发展。正因如此,至金元时期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才被奉为经典。应该说,张仲景的治病思维所以被器重是与理学的哲学思想分不开的。也正因如此,中医学在诊治疾病时,将辨别证候放在第一位,在治疗疾病时亦将调理证候使之达到阴平阳秘,最终达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健康目的。应该说,理学的形成与发展,对中医临床与中医理论的发展均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到了金元时期,著名医家刘完素注重研究张仲景,对张仲景的辨证论治思想十分崇拜,故称张仲景为“医门之孔子,亚圣也”。将仲景称之为圣,将其著作《伤寒论》奉为经典,至此,中医学辨证论治的思想逐渐形成。与之相关,中医方剂学与处方思想也得到了发展,金元医家成无己不仅全面对张仲景《伤寒论》進行注释,而且还首先对仲景《伤寒论》中的代表方剂进行了方解,将中医方剂的组成由经验方的积累转向据理组方。这样,中医的理法方药逐渐得到统一。中医理论与临床从此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中药学的理论建立是与中医学分不开的,中药的发展历史悠久,从《内经》成书时代开始就有大量的中药治病记载,传说在黄帝时代,有“神农嚐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的传说,在《内经》时代,当时并存的方书有十一部,《汉书?艺文志》记载有“经方十一家”,可见中药和复方治病有悠久的历史,与《内经》前后时期出的著作《神农本草经》即记载了中药材三百六十五种,分为上、中、下三品,记录了每味药物的功效主治,在《内经》一书中构架了中药学的理论基础,将药物以阴阳、四气、五味进行分类,如“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寒者热之,热者寒之”“风滛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甘。”等记载。形成了后世将中药的理论基础是“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应该说中药学气味理论的形成是在中国哲学的阴阳五行学说基础上构建的,气味学说理论也是中医药学的基本理论之一。这一指导思想与中药理论体系是一脉相承的。因为,中药理论在对人体健康与疾病的认识上,强调了形而上的整体思维,因此,对中药的认识上亦强调了药物对人体的整体作用,寒、热、温、凉四性(后又补充平性)和酸、苦、甘、辛、咸五味(后又补充了淡味),均是强调了药物对人体作用的总体趋向,升、降、浮、沉四种作用趋势,也是对人体总体作用而言,而药物对疾病的认识仅仅描述其对具体病症的功效,中医对中药的应用强调其对整体的作用,因此,更重视其作用的整体趋势。可以说,中药的治疗作用应分为两部分,其一是作用趋向,可称为药象,有同于中医不称脏腑为脏器而称脏象。其二是对疾病的治疗功效。如止咳、化痰、止痛、驱虫、止泻、止痢等。这两方面的作用,中医在应用时,既要注重其作用趋向,又要使其作用功效合理。这样,中药的使用才能符合中医辨证论治的原理,以此言之,中药学的理论形成亦受到了中国哲学文化的影响。
中医的复方理论早在《内经》时就奠定了理论基础,《素问?至真要大论》有“主病之为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的记载,“风滛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甘”等,制定了去除外邪的药物气味配伍原则,后世又补充了气味配伍、升降开阖配伍等方法,如:张元素在《医学启源》中以气味配伍思维创立当归拈痛汤。吴瑭在《瘟病条辨》中对使用的诸方均注明气味配伍的方法。又如,清代瘟病大家杨栗山在其《伤寒瘟疫条辨》中,创立了著名的方剂升降散就是以升降配伍为处方法则的。君臣佐使配伍、气味配伍、升降开阖配伍三种处方法则的确立,都是以调整人体的整体状态为前提的,其选用药物的原则也是以药物的趋向性为指导的,而这些处方思维的确定,又是以中医理论思维中“形而上”的思想分不开的。由此可见,中医药的理论基础受着中国哲学的深刻影响,而运用中医药理论对疾病的病理、诊断、处方用药等诸多方面间接的亦受到中国哲学的影响。
生命的形成、人体的健康、疾病的产生、疾病的去除是十分复杂的科学范畴,中国古人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以中国丰富发展的哲学思想为指导,构建了中医药学的理论体系,再经过反复的临床实践,不断修正和完善这一理论体系,由于,历代名医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不同,临床实践的经历不同,接受的中医理论与治疗方法不同,面对人们生活的自然环境不同,人们生活的社会环境也不同,再加上中医理论的构建也是不十分完善的,因此,不同时期的医家站在不同角度,对中医理论和临床方药的认知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发挥,这就形成在中医药学发展的长河中,出现了学术上的争鸣,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医各家学说。而中医各家学说的出现又为中医药学的内容增添了奇光异彩,开拓了后学着的理论思维。
从以上可见,中医药学的形成与发展具有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中医药学的理论与中国古代丰富发展的哲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古代哲学是中医药理论形成的思想基础。
- 06-11· 日本川商福至株式会社日
- 06-11· 何处杜鹃啼不歇(一)
- 06-11· [转载]清华百年之际
- 06-11· 入住佳洁旅馆 享受贵宾感
- 06-04· 宏扬德育主旋律培养新世
- 06-04· 净土决疑论(一)
- 06-04· 太虚大师《中国佛学》【
- 06-04· [转载]广东兴宁现惊天强拆
- 06-04· 泰国高僧驾鹤西去肉身不
- 06-03· 【引用】金城-中国近代画
- 06-03· 3D肉蒲团迅雷下载[2011最新
- 06-03· 卫浴洁具价格上涨,原因
- 06-03· 聚焦何巧女:东方园林背后
- 06-03· 东方【时事点评】:2011年
- 06-03· 东方电气董事长王计做客
- 06-03· 东方丽人
- 06-03· 我的妹妹不可能那么可爱
- 06-01· 寻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佗
- 06-01· 今日反恐演练 43条公交绕
- 06-01· 东莞国际机械展览会引来